科学网—黄河九曲
 精选
精选
已有 1004 次阅读
2025-11-8 23:38
| 个人分类: 考察随笔 | 系统分类: 科研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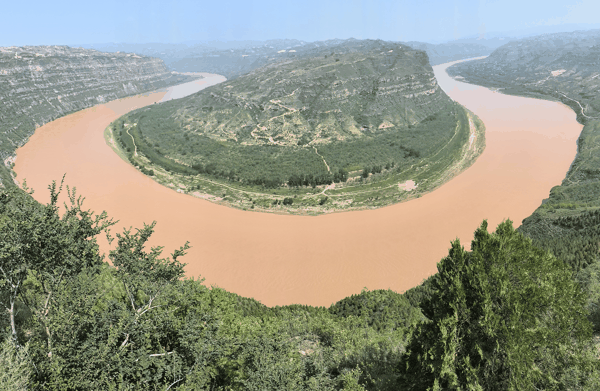
黄河九曲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近纪课题组和榆社县自然资源局组成的联合考察队,结束了在山西榆社盆地的地层古生物考察工作,感受了阴晴多变的夏日气候,也经历在野外被暴雨浇个透心凉的体验后, 2025 年 7 月 12 日,我们将启程前往永和县。车轮碾过清晨的薄雾,三辆车载着整个考察队,早早就出发了。星期六的榆社县城,街道还浸在静谧里,早餐铺飘出的小米粥香气与凉爽的空气交织,为今天的旅程拉开序幕。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寻找一个重要的化石地点。 1923 年,德国古生物学家 H. Killgus 研究发表了一个晚中新世哺乳动物群,其中包括两个新属新种山西副板齿犀 Parelasmotherium schansiense 和塔氏山西兽 Schansitherium tafeli 、一个新种中华马羚 Hippotragus sinensis ,以及鬣狗、无角犀和瞪羚等。从这三个新属种的命名看,显然与中国有关,与山西有关,也与塔氏有关。确实, Killgus 研究的这批材料由德国人 Albert Tafel 于 1905 年在中国晋陕之间的黄河流域考察时采集,被送到德国图宾根大学保存。 Killgus 在他的论文中写道:“这些化石是在黄河附近的山西省 Kutschwan 发现的,产自厚约 100 米的水平红色土状堆积中”。但是问题来了,模式地点的 Kutschwan 的中文是什么?具体位于山西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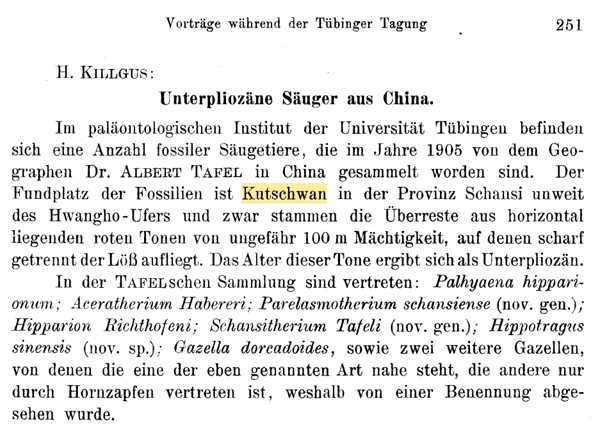
Albert Tafel ( 1876 年 11 月 6 日 -1935 年 4 月 19 日)是 20 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医生、探险家。他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先后在图宾根、柏林和弗赖堡学习医学,并于 1903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还前往克里特岛、阿尔巴尼亚和波斯等地旅行。之后,他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并在其推荐下,于 1903 年加入费通起( Wilhelm Filchner )的考察队前往中国,特别是西藏地区,担任队医。 1905-1908 年, Tafel 根据李希霍芬的建议,独立带队在鄂、陕、晋、内蒙、川、甘、青等省区进行了第二次科学考察,重点考察青藏高原、黄河中上游地区,历时 900 多天。 Tafel 在 1914 年出版了记述他在中国考察经历的两卷本《西藏行记:中国西北、内蒙古和西藏东部科学考察》,并在两年前的 1912 年先出版了 1905-1908 年考察的地图集。

然而,在这本考察记中,虽然有两幅展示众多哺乳动物化石的插图,即 Killgus 研究的标本,但 Tafel 的文字中仅在第 79 页讨论黄河的起源问题时,提到“我在旅途中从这些红土中收集到的头骨和骨骼,属于亚洲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动物群”。没有具体的化石产地,也没有出现 Kutschwan 这个地名。 Killgus 在图宾根显然与 Tafel 有过交流,因此 Kutschwan 这个地名并非空穴来风。

由于没有准确的中文名字,只能根据读音进行推测。首先, Kutschwan 中的 wan 最容易想到是中文的“湾”,而且 Tafel 沿黄河考察,陕西民歌中唱到“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于是,我就从现在的精细地图上顺着晋陕间的黄河在山西一侧寻找有与 Kutschwan 发音接近的“湾”。这样,永和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地名“取材湾”就进入了视野,并且向德国同行咨询了发音,觉得确实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此行就是前往取材湾调查核实。除了发音有可能是这个地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取材湾是否有相关的地层?我们行前特地向山西自然博物馆的续世朝总工求助,他提供的地质图上显示取材湾确实有三趾马红土,即保德组出露。
我们向西行驶,首先沿东吕高速前进,很快就经过榆社的云簇湖。这处人工湖是太行山脉中的一颗明珠,库区水面蜿蜒曲折。清晨的湖面无风,像一块巨大的碧玉铺展在山谷间,远处的山峰轮廓朦胧,还记得前几天野外考察路过岸边时看见芦苇丛里偶尔有水鸟惊飞,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我们在车上也没闲着,继续查找资料,发现 Tafel 考察记中关于川西高原阿坝州的内容被杜轶伦节译为《达菲尔在阿坝》, 2023 年由 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我们就想向译者了解一些情况,到网上一查,没想到 杜轶伦博士就是榆社人,曾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目前在西北工业大学担任教师工作并从事中德交流史的研究。我们考察队中的贡建瑜局长一直在榆社工作,赶紧请他打听能否问到小杜的电话,我同时也请陕师大的王欣教授打听谁曾是小杜的导师,一定会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们继续行驶,车轮转过的地方,风景不断变换。起初是茂密的阔叶林,杨树、槐树在绿意中透着夏天的勃勃生机生机;行至高处,植被渐稀,取而代之的是耐旱的松柏和灌木丛,山体岩石裸露,尽显太行的雄奇险峻。透过车窗望去,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梯田顺着山势层层向上,勾勒出优美的曲线。偶尔能看到山间的小村庄,红瓦白墙的房屋散落在山谷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仿佛世外桃源。
接近中午,我们路过隰县,这里是刘东生先生 1962 年命名早更新世“午城黄土”的地方,地图上标有黄土地质公园,我们当然要去。当地的小镇就叫黄土镇,有许多与黄土有关的宣传标语。公园属于自然状态,没有围起来,但建有瞭望台、步道等设施,并有宣传牌和指路牌。
黄土高原作为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广、厚度最大的地貌单元,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地貌演化及人类活动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天然实验室。黄土地质公园内的剖面出露完整,总厚度达 80 余米,自下而上清晰呈现出午城黄土、离石黄土与马兰黄土的叠覆关系。其中,午城黄土以棕红色为主,质地坚硬,富含钙质结核;离石黄土为棕黄色,夹有数层古土壤层;马兰黄土则呈灰黄色,质地疏松。这套黄土堆积始于早更新世,历经中更新世、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持续时间达 250 万年。

地质公园的残塬沟壑区是黄土高原地貌的典型代表,这是随着流水的长期侵蚀,塬面边缘逐渐被切割,形成了深浅不一的沟壑,呈现出“塬、梁、峁、沟”交错分布的复杂地貌格局。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沟壑两侧的黄土崖壁上发育有大量的垂直节理,部分区域还出现了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遗迹。据当地村民介绍,每逢暴雨季节,沟壑内易发生山洪暴发,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因此,地质公园依托黄土地貌景观、古人类活动遗址等特色资源,开展地质科普宣传活动,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对我们而言,在这里的最主要收获,是知道在命名地点,典型的午城黄土是红色的,而不是一谈到黄土就认为必定是黄色的。已到中午时分,我们就在黄土镇午餐,镇上有婚礼,路旁停满了车,餐厅不接待其他客人。最后终于找到另一家饭馆,发现饭菜量都很大,当面条上来时,不是小碗大碗,而是超级碗。
午后导航到取材湾,沿呼北高速行驶,道路两旁的风景从太行山脉的雄奇逐渐过渡到吕梁山区的苍茫。远处的群山不再陡峭,而是变得舒缓起伏,山坡上种植着大片的玉米地和谷子地。路边的村庄渐渐多了起来,房屋的风格也悄然变化,从晋中地区的红瓦白墙,变成了吕梁山区特有的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冬暖夏凉,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最后一段离开高速公路,转到 520 国道,逐渐从高原面开始下降。快接近黄河时,路的倾斜坡度变得非常陡,而且路面破碎不堪,像是已经废弃。在马头关终于看到黄河,一座高架桥跨河而过,但看起来似乎还未开通。我们再沿 525 县道顺着黄河上游方向行驶几公里,最终抵达地图上标注的取材湾。而取材湾仅仅是一个地名,黄河在这里有一个宽缓的弧度,但并不是一个村庄,没有一户人家居住。附近倒是有一个越野露营地,以及大型的采沙场。

取材湾的黄河岸边出露的都是三叠纪砂岩地层,地质图上标注的保德组在东侧的深沟尾部,没有可通行的道路。而且,保德组应该覆盖于三叠纪地层之上。我们于是再沿一条乡道绕到塬面上,一路上看见许多石油钻井。导航只能通往叫“河里”的村子附近,那里离保德组露头很近,步行不远就能到达。没想到,一座正在施工的钻井恰好布置在河里村边,用推土机新开通了一段简易道路,所以可以直接开车过去。但路非常险峻,在黄土脊的狭窄地段上下蜿蜒,忍不住想下车走过去更安全。

到了井场一问,原来是大港油田的施工队。咨询了他们的地质技术员,但钻井的工作更关注地下深部的地层,对地表的新生代堆积不太了解。于是我们就自己寻找,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黄河岸边延伸上来的三叠纪砂岩,而整个塬面都是第四纪黄土覆盖,夹在两者之间的晚中新世保德组在哪里呢?结果就在旁边,这套红土地层风化后又被风尘披盖,所以与黄土很难区分。我们就在这一小块保德组露头上寻找,张晓晓博士发现一枚啮齿类牙齿化石。不过,完全没有三趾马动物群大哺乳动物化石的线索,也问了这一带的村民,从未听说过挖掘“龙骨”的事,而“龙骨”正是一百多年前 Tafel 等考察者听到当地人对哺乳动物化石的称谓。这一小片红土露头,显然也没有发掘出图宾根大学那样一大批哺乳动物化石的可能。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取材湾是 Kutschwan 的可能。

天色已晚,我们前往永和住宿,日暮时分抵达县城。这座黄河东岸的小城,建在狭窄的沟谷中,看起来非常拥挤。既是街道又是公路的两旁停满轿车,而来来往往的大卡车就在其间艰难地穿行,看起来非常危险。但商铺林立,经济生活非常繁荣,我们就在街边晚餐,对汽车带起来的尘土视而不见。
次日清晨,我们早早起床, 8 点半出发,去黄河乾坤湾的蛇曲地质公园,想看看这个著名的“湾”的特征。由于网上地图只在乾坤湾的陕西一侧有地质公园的标注,我们一开始准备过黄河到那边去。但在加油站放大地图再仔细看,山西这边也有瞭望点,还有配套的博物馆,而且 Killgus 明确表述 Kutschwan 在黄河的山西一侧,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去。
路上经过“东征”村,也有东征纪念馆。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作战,在永和留下了宝贵的史迹。行驶约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乾坤湾地质公园。站在瞭望台上,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黄河形成连续的巨大“ S ”形蛇曲,一共有七个湾,三叠系的岩层被切割得非常陡立,但其上没有晚中新世红土。两岸群山巍峨挺拔,黄河水奔腾不息,浑浊的河水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沧桑,蜿蜒向前。灿烂的阳光洒在河面上,河水泛着金色的波浪,与两岸的绿树、黄土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我们去了地质公园内的博物馆,内容相当丰富,以地质知识为主,也有考古的文物,特别是一组青铜器异常精美。不过,博物馆也存在败笔,将巨型的山西山西鳄( Shansisuchus shansisuchus )的复原骨架说成是小型的桑壁永和鳄( Yonghesuchus sangbiensis )。

离开乾坤湾,对于 Kutschwan 到底在哪里?我们一时失去了追索的方向。这时,贡局长和王欣教授都找到了杜轶伦博士的联系方式,他对 Tafel 的著作相当熟悉。我们立即接通了电话,小杜认为:“应该是 Tafel 从保德去岢岚的路上,在保德附近的山上眺望黄河两岸,提到了红土大量发育的情况和在红土区域搜集到的化石,还提到了‘三趾马层’。可能这些化石是在一大片区域内找到的,不是某个小范围的地点,也有可能横跨山陕两省”。
与此同时,我们车上的史勤勤博士问了 AI ,给出了看似相当合理的推断:“保德桥头镇老地名‘圪稠湾’,山西方言‘圪稠’连读为 Ge-chwan ,德语可能转写为 Kutschwan ”,还提供了保德的“库城墕”和兴县的“枯茨峁”作为候选。我们正高兴有了非常匹配的线索,谁知一查,根本没有这三个地名,全是 AI 的幻觉杜撰的。
看来我们只能暂时放弃追索,再思考如何揭开这个谜题。我们与榆社团队惜别分手,他们返回榆社,我们到榆次与古脊椎所的另一支新近纪考察队会合。在车上我突然想到刚才 AI 的一句话还是很有道理:“查阅图宾根大学档案中 Tafel 的原始标签”,这是一个新的思路。
机会很快就来了,就在不久前的 10 月份,我们课题组的马姣博士赴图宾根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环境地球化学合作研究,我请她特别关注 Tafel 的这批标本。很快,她有了调查结果:首先是这批标本仍然在图宾根大学的妥善保管中,其次是每件标本上都有原始的标签。不过,标签上并无中文信息,也没有 Kutschwan 这个地名。与此同时,马姣发来了 Tafel 考察的地图集,我于是沿着晋陕间黄河从南到北一张一张仔细查找。 Tafel 的地图非常详细,有黄河两岸的测绘地形,很小村庄的名字都有,甚至每个村的人口户数全部标在图上。可惜,上面没有 Kutschwan 。

不过,有一个新的发现,说明我们原来都判断错了。 Kutschwan 中的 tschwan 并不是什么“湾”,整个音节就是一个字“庄”。比如,在陕西韩城附近有 Matschwan 和 Setschwan ,这两个地名及其位置就是今天地图上的“马庄”和“西庄”,其他的 tschwan 也与今天的各个叫“庄”的地名对应。然而,这就很奇怪了,在早期德文图书中,中国的“庄”拼作 t schwang ,例如比 Tafel 更早的李希霍芬的著作中将“魏庄”拼为 Hweitschwang ,但 Tafel 为什么取消了后面的 g ?而后来的德语文献中,“庄”则按威妥玛拼音或邮政拼音拼写为 chuang ,例如师丹斯基( Otto Zdansky ) 1925 年的著作中将山西省武乡县的郝家庄拼写为 Hao-Chia-Chua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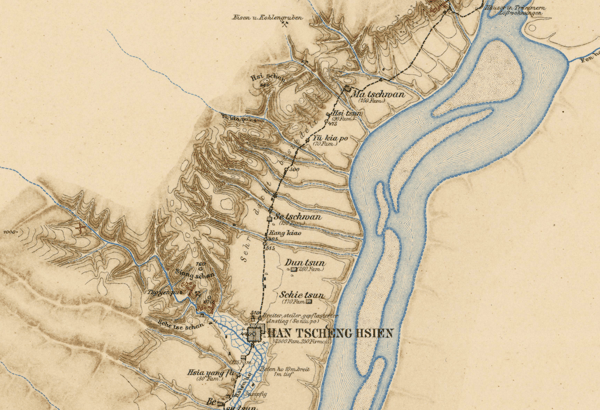
这个 Kutschwan 的“库庄”、“苦庄”还是“顾庄”、“古庄”,它在山西或陕西黄河附近的哪里?下一步将寻找 Tafel 的原始野外记录,但说实在话,看过他的手书,那德文实在分辨不出写的是什么。不管怎样,我们继续追索,未完待续!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邓涛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243751-1509480.html
上一篇: 落叶满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