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改变世界的七个基础科学发现
 精选
精选
已有 502 次阅读
2025-11-7 10:47
| 系统分类: 海外观察
7项改变世界的基础科学发现
奥泽匹克(降糖药)、磁共振成像( MRI)仪器与平板电视,这些成果均源于数十年前的基础研究——而如今,这类研究正遭到美国政府的大幅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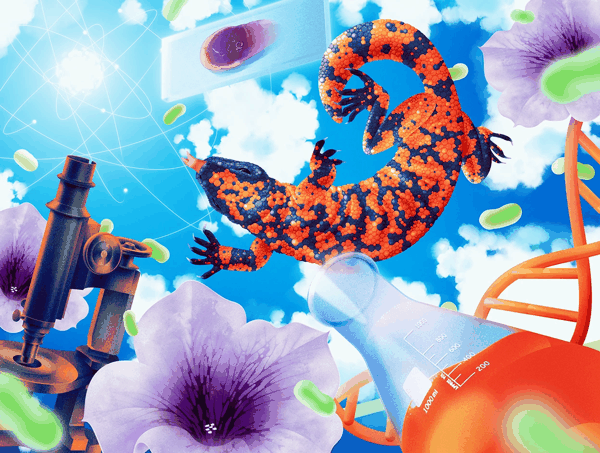
在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正在大幅缩减科学研究投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已削减了近20亿美元的已获批科研资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则终止了超过1400项科研资助项目。此外,总统还计划进一步“掏空”科学界:其提出的2026财年预算提案中,非国防相关的研发资金将被削减36%。
“他们大规模取消了各类尚在进行中的研究项目,”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表示,他曾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担任科学顾问,“如今,他们还打算通过预算削减将这种削减常态化。”
这些被取消或面临削减风险的研究,既包括 “应用类”研究(有明确应用方向,可能具有商业属性),也包括旨在创造新知识的“基础类”或“纯理论”研究(“蓝天研究”)。
基础研究很容易因看似 “不切实际”而遭到质疑,但事实上,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基础研究的投资回报率——即对社会的回报——非常高,通常每投入1美元,就能带来数美元的回报,”霍尔德伦说。
美国的资金削减对基础研究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从历史上看,政府一直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霍尔德伦指出,私营部门绝不会对这类研究投入足够资金: “这类研究的回报周期太长,资助方获取回报的可能性也极具不确定性。正因如此,资助基础研究本质上是政府的责任。”
尽管无法预估联邦资助的削减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未来的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指出,历史上有大量源于基础研究、最终改变世界的成果。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从热泉到 DNA法医鉴定
1966年夏天,当时还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本科生的哈德森·弗里兹(Hudson Freeze),住进了黄石国家公园边缘的一间小屋。他当时在为微生物学家托马斯·布罗克(Thomas Brock)工作——布罗克坚信,某些微生物能在远超预期的高温环境中生存。为了采集热泉中的细菌样本,弗里兹每天都要前往热泉区域,途中还要躲避熊群以及它们造成的“交通堵塞”。

1967年,托马斯·布罗克站在黄石国家公园的蘑菇泉旁。研究人员在该地点发现了能在高温流体中存活的细菌。 图片来源:托马斯·布罗克/美国地质调查局(Thomas Brock/USGS)
9月19日,弗里兹成功培养出了一份来自蘑菇泉的淡黄色微生物样本。在显微镜下,他观察到了从接近沸点的流体中采集到的一系列细胞。“我看到了前人从未见过的东西,”如今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桑福德·伯纳姆·普雷比斯医学发现研究所(Sanford Burnham Prebys Medical Discovery Institute)的弗里兹说,“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当时显微镜下的画面,我仍会起鸡皮疙瘩。”
三年后,弗里兹与布罗克发表论文,描述了其中一种细菌,并将其命名为 “水生栖热菌”(*Thermus aquaticus*)[1]。这种细菌在70°C的环境中生长状态最佳。1970年,两人从水生栖热菌中分离出一种酶[2],这种酶在95°C的最适温度下可参与糖代谢。彼时,弗里兹已进入研究生阶段,研究重心也转向了黏菌,而其他研究者则继续深入研究水生栖热菌。1976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的一个团队从中分离出了另一种酶[3]——一种能在80°C环境下合成新DNA的“DNA聚合酶”。
七年之后,这种被称为 “Taq聚合酶”的物质,恰好满足了生物化学家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发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需求——PCR技术可快速将单个DNA片段复制成千上万份[4]。穆利斯需要高温将DNA分子解旋,因此也需要一种能在高温下工作的聚合酶,以避免反复加热和冷却的繁琐步骤。
如今, PCR技术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应用场景涵盖医学(如匹配器官捐赠者与受赠者、诊断癌症)以及协助警方锁定凶手的DNA指纹鉴定等。
磁共振成像( MRI)的起源
磁共振成像( MRI)是现代医学的支柱技术之一。它能生成人体内部结构的高清图像,例如显示心脏内的异常结构,或肿瘤的增大与缩小情况。其衍生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可追踪大脑中血流的变化,这一技术让研究人员得以深入探索“大脑如何工作”的基本原理。此外,与许多其他成像技术不同,MRI具有无创性,且无需使用放射性物质或电离辐射。
MRI技术源于20世纪30年代对原子核物理特性及其内部基本粒子的研究。“这类研究在当时非常深奥,‘应用前景’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市莱莫恩学院(Le Moyne College)的化学家卡门·朱恩塔(Carmen Giunta)说。

20世纪30年代,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的研究最终为MRI扫描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图片来源:RDB/ullstein bild/Getty Images
MRI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关键发现,与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研究有关。这类粒子具有一种名为“自旋”的特性,可描述其角动量。
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及其同事通过让原子核束穿过磁场,来研究“自旋”现象。在磁场环境中,质子和中子的自旋方向不同,其能量水平也会略有差异。“拉比开发的共振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检测‘自旋在磁场中改变方向’的技术,”朱恩塔解释道。凭借这项研究,拉比于1944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核磁共振( NMR)技术最初应用于化学实验室:由于原子核对周围环境极为敏感,通过精确测量核磁共振信号,可确定原子在大分子中的连接方式。20世纪70年代起,这项技术被改造为生物组织成像工具。保罗·劳特布尔(Paul Lauterbur)与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因在MRI技术研发中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根茎类蔬菜与平板电视
故事始于 1888年初的布拉格:植物学家弗里德里希·赖尼策(Friedrich Reinitzer)从胡萝卜根中提取出了一种名为“胆固醇酯”的化学物质。其中一种物质——苯甲酸胆固醇酯晶体——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特性:普通晶体受热时,会在同一温度下同时失去固体形态和颜色,而这种晶体却不会。“它们在145°C时失去固体形态,但仍保留着蓝色,直到温度达到178°C才会褪去颜色,”法国尼斯市蔚蓝海岸大学(University of the Côte d’Azur)的米歇尔·米托夫(Michel Mitov)说。
此前已有其他研究者观察到过类似现象,但赖尼策意识到,这背后可能存在一种重要的新现象。由于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他在 3月14日给当时德国亚琛市(现属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物理学家奥托·莱曼(Otto Lehmann)写了一封长信。“莱曼是继续并重现这一观察的最佳合作伙伴,”米托夫说,因为莱曼发明了一种带加热台的显微镜,可实时观察晶体的变化。接下来的几周里,两人通过信件和样本交流,赖尼策则在5月于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展示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奥托·莱曼在液晶研究中取得了关键发现,为现代电视和智能手机屏幕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图片来源:佚名(Unknown author)
莱曼的核心发现是:这种晶体失去固体形态后,仍保留着晶体的部分特性,同时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液体的特征。从分子层面看,它们由长链分子构成 ——这些分子既保持着有序排列(类似晶体),又能自由移动(类似液体)。莱曼将其命名为“液晶”。
数十年间,许多研究者拒绝接受这一概念,因为它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用于分类物质的体系相悖 ——传统体系中,物质只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态。液晶模糊了这些界限,而科学界对它的认可“付出了极高的认知成本”,米托夫表示。
20世纪上半叶,液晶存在的证据已无可辩驳,但由于人们认为它毫无实用价值,相关研究逐渐停滞。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化学家才重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1968年,工程师们基于液晶技术研发出了首款平板屏幕,最终催生了平板电视。不过米托夫指出,液晶的应用远不止屏幕——还包括相机、显微镜、智能材料、机器人技术,甚至防伪技术等领域。
基因编辑技术的“微小起点”
“每次看到CRISPR技术的新应用,或是听说它治愈了某人,我都激动得难以自持,”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University of Alicante)的微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莫希卡(Francisco Mojica)说。
CRISPR是“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的缩写,这是一种可对基因组进行精准编辑的工具。它为基础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也为治愈镰状细胞贫血、免疫功能障碍及危及生命的代谢性疾病等遗传性疾病铺平了道路。埃马纽埃尔·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与珍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因研发该技术,共同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而引发这场技术革命的发现,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始。 1989年,当时还是博士生的莫希卡正在研究“地中海盐盒菌R-4”(*Haloferax mediterranei* R-4)——这是一种古菌(单细胞生物),发现于阿利坎特附近的制盐池。他试图弄清这种微生物为何能在高盐环境中存活。在确定了该微生物基因组中几个潜在的关键区域后,莫希卡对其进行了测序,并意外发现其中存在间隔规律的短重复片段。他与其他研究者最初为这些重复片段起了不同的名称,最终统一为缩写“CRISPR”。莫希卡回忆,他当时曾为这些重复片段提出过一些可能的功能,但“事实证明全错了”[5]。

弗朗西斯科·莫希卡(Francisco Mojica)对微生物基因的研究,为CRISPR基因编辑系统的研发奠定了基础。图片来源:胡安·卡洛斯·索勒(Juan Carlos Soler)/ARCHDC/阿贝赛档案馆(Archivo ABC)/阿拉米图片库(Alamy)
后来莫希卡发现,许多不生活在高盐环境中的微生物体内,也存在类似的序列。 “无论这些序列发挥何种作用,都不会与微生物所处的各种特殊环境相关,”他表示。
关键线索来自一项发现:在这些重复片段之间,存在噬菌体(一类感染细菌的病毒)基因组的序列。最终莫希卡意识到,携带某一特定噬菌体序列的细菌,不会被该噬菌体感染。 “我们推断,这是一种适应性免疫系统,”他说,“某个祖先细菌从噬菌体中获得了间隔序列,此后其后代便对该噬菌体感染具有了抵抗力[6]。”
莫希卡知道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此前从未在细菌或古菌中观察到适应性免疫系统。他还认为,这一发现或许能为应对细菌感染提供帮助。随后,其他研究者发现CRISPR的作用机制是在特定位点切割DNA[7]。在此基础上,杜德纳(Doudna)与沙尔庞捷(Charpentier)弄清了如何利用这一系统,并对其进行“重新编程”以实现基因编辑。CRISPR革命就此拉开序幕[8]。
受蜥蜴启发的减重方案
奥泽匹克( Ozempic)等减重与降糖药物已成为当下的“神奇药物”。美国有近5%的人使用这类药物减重,到2030年,这类药物的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000亿美元。尽管推动这类药物研发的大部分工作以医疗应用为目标,但其中一项关键发现,却源于对美国唯一一种有毒蜥蜴——希拉毒蜥(*Heloderma suspectum*)的研究。

希拉毒蜥体内的一种肽,为GLP-1类药物的研发提供了助力。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库(Getty)
这一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名为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的分子,它由人体肠道产生。20世纪80年代,化学家斯维特拉娜·莫伊索夫(Svetlana Mojsov)发现,GLP-1能刺激胰岛素分泌,从而降低血糖水平[9]。
现任职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丹尼尔 ·德拉克(Daniel Drucker)曾与莫伊索夫合作开展这项早期研究。“当时我们关注的是它在糖尿病治疗方面的潜力,”他说,“十年后的1996年,我们与其他团队共同发现,GLP-1能减少食物摄入,其减重潜力也随之显现。”但问题也随之而来:GLP-1的半衰期极短,仅为数分钟。这意味着它无法直接作为药物使用——因为在发挥显著作用前,它就会在体内被分解。
于是,德拉克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 GLP-1的受体(正是这种受体介导了GLP-1对胰岛素的调节作用)。或许,他们可以通过靶向这一受体来发挥作用。
这便是蜥蜴 “登场”的契机。希拉毒蜥生活在美国西南部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尽管名字带“毒”且确实有毒,但其行动迟缓,对人类相对无害。1992年,由纽约市退伍军人事务医疗中心的让-皮埃尔·劳夫曼(Jean-Pierre Raufman)带领的团队,从希拉毒蜥的毒液中发现了一种名为“艾塞那肽-4(exendin-4)”的肽[10]。由于艾塞那肽-4与GLP-1结构十分相似,德拉克开始研究它是否能与GLP-1受体结合,从而模拟GLP-1的功能[11]。
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 2008年,德拉克主导了基于该发现研发的药物“艾塞那肽(exenatide)”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艾塞那肽不仅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帮助患者减重[12]。
此后,更多 GLP-1受体激动剂相继问世,而后续的减重药物发展历程,便已载入史册。
催生新药的花朵
今年 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一种名为“菲图希兰(fitusiran)”的药物。该药物用于治疗两种主要类型的血友病——这是一种凝血功能障碍疾病,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出血。菲图希兰是一类新型药物中的最新成员,这类药物利用小段RNA干扰基因的表达。
菲图希兰等 RNA干扰(RNAi)药物,是三十多年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始于一次偶然的观察,随后通过细致的基础研究逐步深入。

对紫色矮牵牛的研究,为RNA干扰现象的发现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库(Getty)
研究的起点是 1990年由理查德·约根森(Richard Jorgensen)主导的一项研究——当时他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DNA植物技术公司(DNA Plant Technology)。为弄清基因调控机制,约根森与同事尝试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紫色矮牵牛:他们向矮牵牛中转入了第二个控制色素合成的基因,希望让花朵颜色更鲜艳。但令他们意外的是,实验结果并未得到颜色更深的紫色矮牵牛,反而培育出了白色矮牵牛[13]。“造成这一现象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团队在论文中写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研究者们深入探究这一现象,发现向细胞内注射小段 RNA就能触发该现象。接着在1998年,现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安德鲁·法尔(Andrew Fire)、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的克雷格·梅洛(Craig Mello)及其同事,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机制。他们发现,小段双链RNA可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触发信使RNA(mRNA)的降解;而mRNA是合成蛋白质的模板,因此降解mRNA会阻止相应蛋白质的生成[14]。
凭借这项研究,法尔与梅洛共同获得了 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类全新的药物也由此诞生。
远古陨石与洁净空气
20世纪50年代,地球化学家克莱尔·帕特森(Clair Patterson)被“铅”的问题所困扰。而他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工作,最终帮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当时,帕特森正试图开发一种利用铀和钍的放射性衰变法测定岩石年龄的方法。数十亿年来,这些元素会发生裂变形成更小的原子,最终衰变为铅的不同同位素。通过测量不同铅同位素的比例,帕特森得以确定远古岩石的年龄 [15]。

克莱尔·帕特森(Clair Patterson)通过测定远古岩石年龄的研究,助力确定了环境中铅污染的来源。图片由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提供
然而,帕特森当时不得不应对铅污染的问题。他所在的机构是位于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而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极高。 “加利福尼亚处于一个盆地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环境健康科学家杰罗姆·恩里亚古(Jerome Nriagu)解释道,这种地理特征会导致污染物不断积聚。为此,帕特森不得不建造一座“洁净实验室”,对所有进入实验室的空气进行过滤。
尽管面临这些困难,帕特森仍成功地以极高精度测定了迪亚布洛峡谷陨石(即形成亚利桑那州陨石坑的天体)及其他多颗陨石的年龄。他发现,这些陨石的年龄均为 45.5亿年。由于科学界认为陨石与地球形成于同一时期,这些测量结果确定了地球的年龄——此前通过精度较低的研究得出的地球年龄并不准确。1953年,帕特森在一次会议上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并于1956年发表相关论文[16]。
在解开这一重大科学谜题后,帕特森将注意力转向了铅污染问题:这些铅污染来自何处?是否具有危害性?
帕特森怀疑污染源是含铅汽油。他与地球化学家 Mitsunobu Tatsumoto 合作,耗时数年才证实了这一猜想。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帕特森和 Mitsunobu Tatsumoto 指出,铅污染已扩散至海洋最偏远的区域,且几个世纪前的环境铅含量远低于当时[17]。这一结论引发了与铅产业的激烈对抗——铅产业极力抵制该研究结果,但最终各国还是颁布了含铅汽油禁令。据估算,这项禁令每年可挽救超过100万人的生命,并节省数万亿美元的社会成本。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1174-1508039.html
上一篇: 寿命超过200岁的弓头鲸DNA强修复力的秘密 下一篇: 富氢次氯酸水对肉鸡饮水细菌水平、生长性能、抗氧化能力及肠道环境的影响
